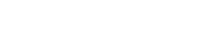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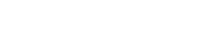

1970-01-01 08:33:29
托收(collection)是指银行按照委托人(一般为出口商)的委托指示办理金融单据或/和商业单据以便得到付款人(一般为进口商)承兑或付款,或凭承兑或付款交出商业单据,或凭其他条件交出单据的一种结算方式,[i]简而言之,其基本做法是指由卖方对买方开立汇票,委托银行向买方收取货款。按照托收是否附有商业单据可以将其分为光票托收(clean collection)和跟单托收(Documentary collection),其中后者是国际贸易中常用的托收方式。在跟单托收中,由于交单条件的不同,又可以分为付款交单 D/P ( documents against payment) 和承兑交单 D/A ( documents against acceptance),其中承兑交单只适用于远期汇票的托收。而付款交单还可以作进一步的分类,分为即期付款交单和远期付款交单。由于托收这一结算方式可以加速资金周转,减少费用支出,因此在国际贸易中常被采用。
在整个托收结算流程中,无论是作为托收行(Remitting Bank)、还是代收行(Collecting Bank)抑或提示行(presenting bank),银行都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托收在本质上是一种商业信用,并非银行信用,这也就决定了对于付款人的拒付或拒绝承兑,银行均不承担任何责任,银行所应做到的是善意的、合理谨慎地办理相关业务,[ii]通说认为托收其本质上乃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因此无论是托收行还是代收行如果未履行委托协议中的义务,尤其是没有尽到善意的、合理谨慎的义务,造成委托人(Principal)损失,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下文即将讨论的就是代收行因过错致委托人损失而承担法律责任的案例。
一、据以研究的案例
1998年1月22日,飞奥公司以电传方式通知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外贸公司称,其已于当日向武进外贸公司发送一批货物,船名“MED KEELUNG”,从意大利热那亚到中国汕头,提单号980035/1,日期为1998年1月22日,货物2箱。同年2月23日,圣保罗都灵银行向武进农行发出面函指示:委托人为飞奥公司,代收行为武进农行,付款人为武进外贸公司,到期日为见单后150天,金额为198315.76美元;所附单据包括商业发票、正本提单、海运单、装箱单、数量证明、品质证明和复本传真,用以证明发票NO.71554项下的货物;交单指示为Promissory payment at 150 days at sight(20.08.1998);特别指示——确认收到单据并通过全球财务通讯系统(SWIFT)或以电传方式,确认见单150天(20.08.1998)约定(承诺)款项的支付;在本委托书内容没有抵触的范围内,本委托书适用《托收统一规则》(国际商会522号出版物)。所附单据中,商业发票的号码为NO.71554,日期1997年12月22日,抬头武进外贸公司,付款条款为自起运日起150天信用证,总价值198315.76美元;提单(号码为980035/1)载明的收货人为根据指令,被通知人汕头自由贸易区双龙有限公司,船名MED KEELUNG,装货港意大利热那亚,卸货港中国汕头等。
武进农行于1998年3月18日收到上述全部单据。翌日,武进对外经济技术贸易总公司(以下简称技术公司)使用武进外贸公司02号法人印章、以武进外贸公司名义向武进农行出具一份保函,内容:“我司信用证号D/P 150 DAYS SIGHT,金额为198315.76美元项下之全套单据现已到达贵部,我司保证立即接受该全套单据并予以承兑,且保证在贵部对外付汇前,及时把全额货款打入贵部账户,保证贵部按时对外付汇,如有延期付汇所引起的一切责任由我司承担。”武进农行遂于当日将上述单据交给了武进外贸公司。
1998年3月13日,飞奥公司向武进外贸公司发出传真一份,载明:1998年3月13日签发的第594002859号中国远洋运输公司的提单和下列货物已随“皇后号”海轮由意大利运到中国汕头,航程为76天,所附货物以信用证及97010号合同为准。1998年3月26日,圣保罗都灵银行又向武进农行发出书面指示:委托人为飞奥公司,代收行为武进农行,付款人为武进外贸公司、金额为80369.95美元;所附单据:正本提单、海运单、装箱单、数量证明、品质证明、复本传真、商业发票、产地证和详细交货单,用以证明发票NO.80165、80166项下之货物;交单指示为Promissory payment at 90 days at sight(23.06.1998)90 dd at sight。该指示的内容与1998年2月23日指示内容相同。开具给武进外贸公司的票号为80165和80166的两张商业发票总额分别为51853..54美元和28516.41美元,付款方式为见票后90天即付信用证并以离岸价交付。提单载明的托运人为飞奥公司、收货人为凭指示、被通知方为汕头自由贸易区双龙有限公司。
1998年3月31日,上述单据抵达武进农行。同年4月10日,武进外贸公司向武进农行国际业务部申请延期,要求将付款方式D/P 90 DAYS SIGHT 改为D/P 150 DAYS SIGHT 。武进农行收到延期申请后,于4月14日以SWIFT方式致函圣保罗都灵银行,要求将付款期限改成见票后150天。圣保罗都灵银行于4月20日复函,同意付款期限改为见票后150天如约(承诺)付款交单,并要求通知单据交付时间和确认到期日期。当日,武进外贸公司向武进农行国际业务部出具保函,该保函除金额为80369.95美元外,其余内容与前述1998年3月19日保函相同。武进农行接受该保函,并于同日将上述单据交给了武进外贸公司。
上述托收指示规定的付款期限届满后,武进外贸公司并未将上述两笔198315.76美元和80369.95的货款汇付给武进农行,武进农行也未向圣保罗都灵银行汇款。
意大利飞奥公司遂诉请法院判令武进外贸公司支付货款278685.71美元(折合人民币2304730.82元);武进农行承担连带责任;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另查,使用武进外贸公司02号法人章的技术公司已于2000年9月因停止经营活动满1年,被武进市工商局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由其上级主管部门武汉外经局对其债务承担清理责任。原告飞奥公司遂又追加武汉外经局为被告参加诉讼。
二、裁判要旨
一审法院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飞奥公司与武进外贸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双方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的有关规定,应认定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有效,武进外贸公司依法应向飞奥公司支付货款。技术公司作为该二单业务的具体运作企业,因不具备进出口经营权,而以武进外贸公司的名义操作,属借权经营,且飞奥公司对此也不知道,故技术公司与武进外贸公司依法应对飞奥公司货款的支付承担连带责任。鉴于技术公司已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武进外经局作为技术公司的主管单位,依法应对技术公司的资产进行清理,并以清理后的资产偿付飞奥公司的货款。代收行武进农行在整个托收结算中,属飞奥公司代理人的代理人,与飞奥公司不存在直接的合同关系,飞奥公司无权迳直向武进农行提起诉讼,且武进农行在托收结算中无过错,故飞奥公司要求武进农行承担付款的连带责任于法无据,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三条、《托收统一规则》之规定,判决:一、武进外经局在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对技术公司的资产进行清理,并以清理后的资产向飞奥公司偿付货款278685.71美元(折合人民币2304730.82元);二、武进外贸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案件审理费21534元,由武进外经局负担。
原审原告意大利飞奥公司和原审被告常州市武进外经局不服一审判决先后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述。
二审法院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托收法律关系本质上为复代理关系(再代理或转委托),在托收关系中,既然代收行处理托收事项的风险由委托人直接承担,则委托人当然有权就代收行在处理托收事项过程中的过错所造成的损失直接主张权利。因此,原审法院关于“武进农行作为飞奥公司代理人的代理人,其与飞奥公司不存在直接的合同关系,飞奥公司不能直接起诉武进农行”的认定不符合法律基本原则,应予纠正。武进农行在未能正确理解托收指示的交单条件、又未向托收行圣保罗都灵银行进行询问、且未收到付款人款项的情况下,就擅自交付单据,违反了URC第9条规定的善意和合理的谨慎义务,主观上存在过错,对由此给委托人飞奥公司造成的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但武进农行作为代收行并不负有向委托人保证付款的第一性的付款责任,只是因为其在执行托收指示的过程中的过错行为造成委托人不能及时获得作为基础合同买方的武进外贸公司的货款,因此,在飞奥公司同时向买方和代收行主张权利的情况下,代收行只应在买方不能支付货款的情况下承担赔偿责任。据此,二审法院在维持一审法院判决书第一、二项判决的基础上,又判决武进农行应在武进外经局承担清理责任和武进外贸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后仍不能清偿债务的情况下对飞奥公司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三、分析检讨
由于本案涉及到如何理解国际贸易的中的一些国际惯例,因此本案的审理裁判对于主审法官的国际视野、把握国际规则以及阐释规则的能力都有着相当高的要求。尽管本案的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对于国际规则的理解领悟有所差异,导致了一审判决和二审判决有所不同,但可以说两级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尤其是在判决书的说理部分都充分展示了法官个人良好的理论素养和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从判决结果来看,笔者以为,二审法院的判决准确的把握了《托收统一规则》(Uniform Rules for Collection)第522号出版物(以下简称URC522)的精神实质以及国际贸易中的一些惯例,对整个案件做出了较为恰当的判决,对于我国法院在今后处理类似问题提供了具有借鉴意义的良好范本!尽管案件本身已经尘埃落定,但是就案件本身来看,其中还是蕴涵了较多具有理论思考价值的问题,可以做进一步的深入考察、分析和研究。
应该看到,自从《托收统一规则》(URC522)1996年生效之后,该规则已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所采用,成为国际通行的一项规则。根据《托收统一规则》(URC522)第1条第a款的规定:“该规则适用于本办法第2条定义的、在第四条所指’托收指示’正文中列明了本规则的所有托收业务。除非另有明确约定或与不得违反的一国、一州或当地法律和/或法规相抵触, 本规则对有关各方都具有约束力。”在本案中,托收行圣保罗都灵银行在发给武进农行的指示中载明,在本委托书的内容没有抵触的范围内,本委托书适用《托收统一规则》,按照1996年1月生效的国际商会522号出版物。因此本案关于托收这一具体事项的裁决判断适用URC522条是毫无疑义的。讼争当事人在对这一前提达成基本共识之后,本案一审、二审以及当事人之间的主要论争焦点集中在以下两大问题:
(一)交单条件的类型分析
1、本案交单指示书翻译歧义的澄清
本案中的交单指示为:“Promissory payment at 150 days at sight(20.08.1998)”。由于该指示的中文翻译中存在着歧义,使本案的审理更增加了困难。对此飞奥公司和一审法院分别做了两种不同的理解:飞奥公司将该交单条件理解为“150天远期付款交单”;一审法院将其理解为“见单后150天付款的承诺交单”,两种不同的理解也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交单条件。
仔细分析上述对英文交单指示文字不同翻译,两种不同译法的分歧点在于对“Promissory”一词的不同理解,按照《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辞典》的解释,“Promissory”可以理解为:“约定的;应许的” [iii],按照金山词霸2002年版的解释是“允诺的, 约定的, 有约束力的”。这些解释也就可以将“Promissory payment”理解为“约定款项的支付”或者是“承诺款项的支付”。采用后一种译法在中文中又因为对词性的不同把握极容易产生新的歧义,因为在中文中,“承诺”一词既可以作为一个形容词承担定语修饰的功能,也可以作为动词承担谓语的功能。按照前一种理解,“承诺款项的支付”是指“支付(事先)承诺的款项”;而按照后一种的理解,“承诺款项的支付”是指“付款人承诺支付一定的款项”,变成了承诺交单,两种理解似乎都有一定的合理性,难以断定熟是熟非。但这种中文运用上的歧义性显然误会了英文交单指示的原始涵义,因为在英文交单指示中“Promissory”的的确确是一个形容词,将其翻译成中文也只能作为一个形容词充当定语的限定功能,不应该将其动词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Promissory payment”只能理解为一种支付事先约定承诺的款项的行为,也就是说只有按照前一种的理解才是唯一正解。而且去除“Promissory payment at 150 days at sight(20.08.1998)”定语,拿出该指示的主干成分“payment at XX days at sight”,相信我们对该指示所表明的交单条件就能更为清楚,这显然是一个典型的远期付款交单指示。[iv]
其实抛开对交单指示不同译法的争议,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对于交单指示也能做出更符合当事人真意的理解。因为在付款人武进外贸公司向托收行出具的保函列明为D/P,一审法院认为该指示“属圣保罗都灵银行有权发出指示之外的其他人的陈述”,“对武进农行不具约束力”,话虽不错,也符合URC522的相关规则,然而,这并不妨碍法院及其当事人在理解交单指示时予以参照,一审法院在理解交单指示时对于付款人在来往信函中明确指出的“D/P”不予认可,而仅仅是通过对英文交单指示的单方面的理解就推论出本案中的交单条件为“以其他条款和条件交出单据”,显然有失片面。二审法院综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和URC522规则关于交单条件的规定认定圣保罗都灵银行给武进农行的托收指示的交单条件应理解为D/P(付款交单)是比较准确的。
2、本案属于URC522规定的何种交单条件?
在本案两级法院的审理过程中,都援引了URC522的第7条作为裁判依据,由于本案的交单指示书中所规定的交单条件并非是URC522第7条所规定的典型形式,因此两级法院分别对该条进行了扩张推演。然而对同一条的类推,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却得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结论: 一审法院认为,该分条陈述的是托收包含在将来日期付款的汇票,即应有金融单据的伴随,如无汇票的伴随,则不应据此推出没有陈述是D/A还是D/P,即为D/P的结论。……(而本案交单指示)符合URC522规定的允许D/A、D/P托收之外的“以其他条款和条件交出单据”的要求;二审法院则认为,附有金融单据的远期付款交单已被视为D/P,本案中虽不附有金融单据,但文字内容上最接近于远期付款交单的跟单托收指示当然也应理解为D/P。
要对上述两个类推结论作出准确的评判,需要我们对URC522规则所规定的整个交单条件分类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托收统一规则》(URC522)对交单条件做了两种基本的分类,即:付款交单 D/P ( documents against payment) 和承兑交单 D/A ( documents against acceptance)[v],其中付款交单还可以作进一步的分类,分为即期付款交单(D/P at sight)和远期付款交单(D/P at xx days after sight)。除了上述两种基本分类之外,URC522还规定了一个“凭其他条件交单”。一般认为《托收统一规则》设立了这么一个兜底性的条款是为了使该规则保持一定的开放性,从而表明URC522对于当事人一致认可的其他交单条件的法律效力也是予以认可,也有益于URC522在更大范围内得到认可和适用。如何理解URC522中规定的“凭其他条件交单”?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不能为承兑交单(D/A)、付款交单(D/P)所涵盖的其他交单条件。在本案中,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不应该适用URC第7条的规定,因此将本案中的交单条件理解为“以其他条款和条件交出单据”的形式。我们认为对于这一结论必须可以分解为以下两个问题分别进行推敲:第一,本案是否不能适用URC第7条?第二,本案中的交单指示是否真的不能为承兑交单(D/A)、付款交单(D/P)所涵盖,从而属于“凭其他条件交单”的交单类型呢?
我们先来具体分析本案审理中为两级法院所援引的URC522第7条的规定。正如一审法院所说,URC522第7条是规范附有金融单据的远期付款或承兑交单条件的处理规则,该规定原则上排除了在含有远期付款汇票的同时又含有凭付款交付商业单据的这种交单指示条件,也就是说原则上排除了附有金融单据的远期付款交单(D/P at xx days after sight)这一方式。但此禁止并非绝对,在遇有委托人做出此种指示的情况时,该条规定:“(b)如果托收包含远期付款的汇票, 托收指示应该表明是凭承兑(D/A)还是凭付款(D/P)向受票人交出商业单据。如无此类表述, 则只能凭付款交付商业单据,代收行对交单延误造成的任何后果并不负责。”“(c)如果托收包含远期付款的汇票, 且托收指示表明商业单据凭付款交付, 只能凭付款交单,代收行对由于交单延误造成的任何后果并不负责。” 该两款规定的一个共同倾向是对于包含远期付款汇票的托收原则上按照D/P处理,除非托收指示中有明确的凭承兑(D/A)向受票人交出商业单据的类似表述[vi]。做出这一规定的情况也主要是从降低委托人(出口商)的商业风险来考虑的。一方面由于在远期D/P的情况下,付款到期日和货物到达日并不完全一致,在付款到期日早于货物到达日的情况下,付款人(进口商)无法付款赎单以至不能提取货物的情况下,货物由于得不到妥善处置较易遭受损失;另一方面,在付款到期日晚于货物到达日的情况下,采取D/A的方式将使出口人也就是委托人面临更大的到期不能收款的风险。因此URC522这一规定在原则上禁止远期付款交单(D/P at xx days after sight)这种方式的情况下,又将远期付款交单(D/P at xx days after sight)这一方式作为一种主要的方式,这的确是绕有趣味。
应该看到的是,在URC522第7条仅仅是对含有远期付款汇票的托收交单条件做出了规定,并没有对未附金融单据而仅有商业单据的跟单托收做出规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审法院的判断是正确的,但并不能据此就推论出“以其他条款和条件交出单据”,因为本条仅仅是规范含有远期付款汇票的托收交单条件,并没有规范所有不符合D/P或D/A的情形,我们认为URC522第7条专条对附有金融单据的跟单托收做出如是规定并不表明URC522对于仅附有商业单据的托收不予规范,而仅仅是认为其与一般的跟单托收相比不具备特殊性,托收人和代收行直接按照委托人的指示进行办理即可。因此在本案不能适用该条规范的情况下,还可能适用URC522中关于D/P或D/A的其他一般性规定。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审法院的推论在逻辑上失之严密。但能否如二审法院一样将URC第7条规定类推适用于未附有金融单据而仅有商业单据的跟单托收呢?我们认为,本案中的交单条件应为D/P,但得出这一结论不能也无需通过类推适用URC522第7条的规定。理由如下:
由于本案中的托收是不附有金融单据而是仅有商业单据的跟单托收,因此与URC522规则第7条所规定的含有远期付款的汇票的情形并不一样,因此不宜直接套用URC522规则第7条的规定。二审法院通过类推URC522规则第7条的规定将本案的托收指示视为D/P,这一推演过程过于繁琐,纯属多余,从逻辑上考察同样失之严密。根据逻辑学上的基本原理,当原命题为真时,其逆反命题亦为真,然而反命题却未必为真。如果将URC522第7条关于附有金融单据的远期付款交单视为D/P这一原命题作为真命题的话,并不必然推导出没有附有金融单据的远期付款交单也视为D/P这一命题为真。同样也不能通过适用类推中“举重以明轻”的规则推演出二审法院得出的结论,因为在托收中很难在附有金融单据的远期付款交单和不附有金融单据的远期付款交单中清晰地比较出一个轻重,因此也无法因为附有金融单据的远期付款交单视为D/P,就得出不附有金融单据的远期付款交单也视为D/P的结论出来。
还有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在于,一、二审法院以及很多研究URC522交单条件的人员过于关注URC522第7条的规定,以致于忽略了URC522第6条的规定。本案的托收指示清清楚楚表明是一个典型的远期付款交单(D/P at xx days after sight)方式,而且由于该方式并不包含远期付款的汇票,也不在URC522第7条所禁止的情形之列,代收行直接按照这种不含有远期付款汇票的付款交单(D/P at xx days after sight)方式执行即可。根据URC522第6条的规定:“如果是见单即付的单据,提示行必须立即办理提示付款,不得延误;如果不是即期而是远期付款单据,提示行必须在要求承兑时毫不拖延地提示承兑,在要求付款时,不应晚于适当的到期日办理提示付款。”[vii]。该条将见单即付/承兑分为了见单即付和见单远期付款,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该条所规定的见单付款情形并没有如URC522第7条所规定的附有金融单据的这一特殊要求,也就是说该条规定适用于所有附有或不附有金融单据的情况,成为见单即付的一般性规定。其实本案的情况正属于该条所规定的托收单据是凭单在即期以外的某一期限付款的情形,因此也属于URC522规则调整范围之内的情形,并不需要过多的借助对URC第7条进行类推。
3、代收行的过错及其责任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再考察本案中作为代收行的武进农行是否具有过错。应该说,其过错是较为明显的。
首先,武进农行对托收指示的交单条件理解错误。URC522第4条明确规定了“作出托收指示的一方, 有责任保证清楚而不含糊地表述交单条款, 否则,银行对由此产生的任何结果不负责任。” 然而就本案而言,难谓委托人意大利飞奥公司做出的托收指示含糊不清!前文述及,本案的托收指示清清楚楚表明是一个远期付款交单(D/P at xx days after sight)方式,而且付款人武汉外贸公司在给武进农行的传真以及保函中都出现了“D/P”字样,对交单条件的理解错误,其责任应该在武进农行一方。
其次,武进农行没有严格、正确的按照托收指示执行。根据URC522第1条规定, 银行并无义务处理托收或任何托收指示或以后的有关指示。但是如代收行同意代收就应按托收指示书的指示办理业务,在托收指示不明确的情况下,代收行应及时与托收行取得联系,进一步明确交单条件,否则代收行将承担由此产生的责任。本案中,武进农行由于托收指示理解错误,也没有进一步询问托收行圣保罗都灵银行,在未收到付款人武汉外贸公司款项的情况下擅自交付单据,没有正确的按照托收指示执行,应该对由此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
综合上述分析,显然代收行武进农行违背了URC522第9条所规定的善意和合理的谨慎义务,对由此造成的损失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一结论与二审法院对此所作出的判断是相吻合的。
(二)委托代理抑或其他?
在本案中,一审法院采纳了一审被告武进农行的答辩意见,认为代收行武进农行在整个托收结算中,属飞奥公司代理人的代理人,与飞奥公司不存在直接的合同关系,飞奥公司无权迳直向武进农行提起诉讼。而二审法院对该理由进行了否定,认为托收法律关系本质上为复代理关系(再代理或转委托),在托收关系中,既然代收行处理托收事项的风险由委托人直接承担,则委托人当然有权就代收行在处理托收事项过程中的过错所造成的损失直接主张权利。这种争论不独在本案中,在托收许多类似的案件中都曾发生。由于在托收业务中经常涉及四方当事人:委托人(Principle)、托收行(Remitting Bank)、代收行(Collection Bank)[viii]、付款人(Drawee),对于几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的性质,URC522规则并没有作出明确具体规定,需要研究者及实践者结合URC规则的具体内容和各国民商事法律体系及理论作出界定。因此关于托收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实在有必要进行理论上的澄清和阐释,以期对审判实践提供理论上的指导意义。
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委托人和托收行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的定性并没有太多的争议,本文对此不予展开作进一步的讨论。在托收法律关系争议比较大的是关于委托人、托收行与代收行之间的三重关系如何认识,尤其是对于委托人和代收行之间法律关系的认识分歧较大。传统观点认为托收行和代收行之间的关系是委托代理关系;代收行是委托人代理人(即托收行)的代理人,其与委托人并没有直接合同关系,如果代收行违反托收行的委托书的指示行事,致使委托人的利益受损,委托人无法直接对代收行起诉,只能通过托收行对其起诉。[ix]应该说这一认识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相当一部分的人所认可和接受,也成为本案一审判决的学理基础。但这种认识在当今国际托收实践中遭到了质疑和挑战,也是本案审理中涉及的一个焦点问题。因此实在有必要基于URC522对这些托收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作进一步的梳理。
就托收行与代收行之间的关系而言,我们认为不能一概而论,必须区别代收行由不同主体指定的情况作出分别考察。因为按照URC522第5条的规定,代收行可以由委托人指定,如果委托人没有指定, 托收行可以自己选择符合条件的银行作为代收行。
在代收行是委托人指定的情况下,应该认定代收行也是出口商(委托人)的代理人,由于托收行与代收行均是委托人所委托的代理人,共同完成委托人所委托的向付款人收取货款的任务。尽管托收行和代收行在此托收业务中分工有所不同,托收行仍然要承担一个代表委托人发出托收指示的任务,但托收行和代收行也仅仅是一种业务上的分工合作关系,不宜称代收行是托收行的代理人。
在代收行是由托收行自己选择的情况下,这也是托收业务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情形,代收行是否又如通说所认为的是托收行的代理人呢?我们认为,认定代收行是托收行的代理人有失偏颇。理由在于:依据代理法的基本原理,无论是直接代理还是间接代理,亦无论是隐名代理还是显名代理,代理人要么是以自己的名义要么是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为被代理人的利益行事,决无以其他第三人的名义行事的代理行为。而在代收行是由托收行指定的情况下,如果据此得出代收人为托收行之代理人,那么根据代理法的一般原理,在直接代理的情况下,代收人应该是以被代理人也就是托收行的名义为代理行为,即使在间接代理的情况下也应该是以代收行自己的名义为代理行为,然而事实上,在托收业务流程中,代收行仍然是以委托人(即托收行和代收行这个所谓的代理结构之外的第三人)的名义,向付款人做承兑或付款提示以及接受付款人的承兑或付款;如果付款人拒绝承兑汇票或按汇票付款,代收行不能以自己的名义起诉,而只能将该情况通知托收行,再由托收行通知委托人,由委托人向付款人追偿。因此认定代收行为托收行的代理人是有违代理法基本原理,也不符合托收中的业务流程。
作者:王利明 熊谞龙
编辑(编纂): 上海涉外律师网
说明:上海涉外律师网定期、不定期的选取一些质量较高的相关法律论文、调研成果、法制报道在本网站发布。考虑到绝大多数网站浏览者不具有法律教育背景,为了浏览者更好地理解相关文章,我们会对部分专业性很强的文章进行适当编辑,包括文字修改或文章机构的调整,使发布的文章通俗易懂。在发布前,我们一般会取得著作权人的口头或书面授权。对于部分文章因与作者难以取得联系未取得作者授权而在网站发布的,我们承诺一经作者指出,我们将立即删除;给作者造成损失的,我们依法承担法律责任。